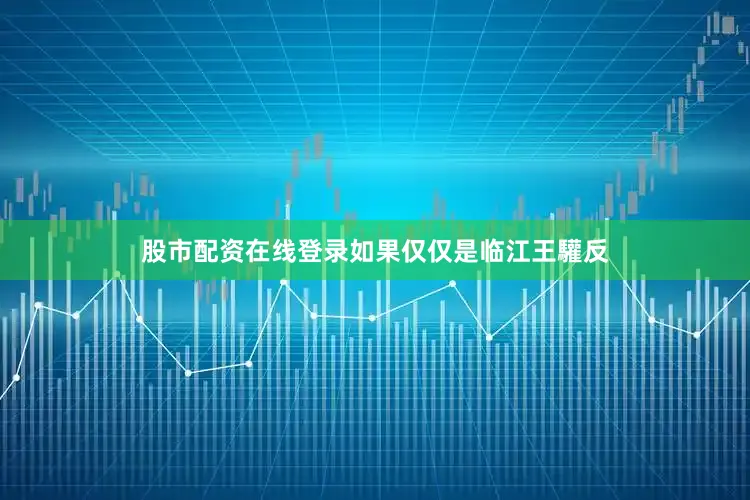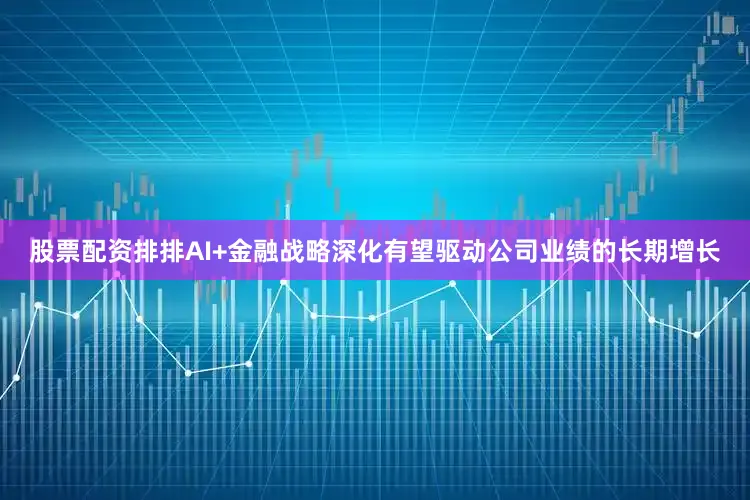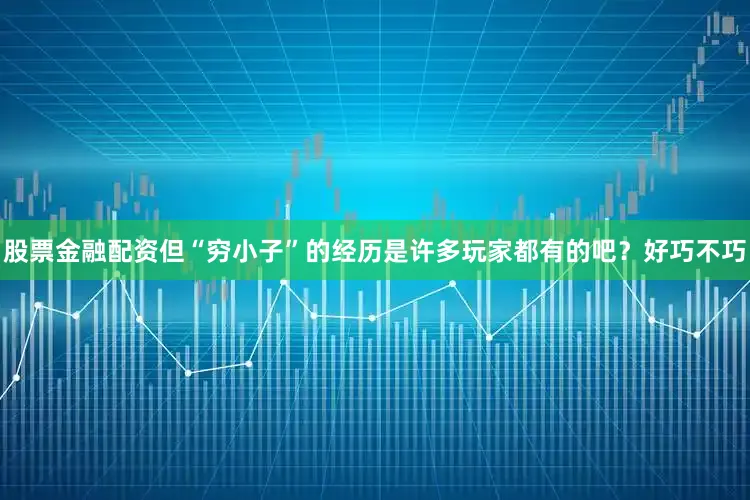
男女+金钱,或许是大部分互联网内容的流量密码。这一点放在《捞女游戏》的爆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6月19日,《捞女游戏》上架Steam,首日便冲上微博热搜。“捞女”一词原本是网络用语,指代通过情感关系索取物质利益的女性个体。“物化女性”“挑动性别对立”的批评声音也随之而来,其后,游戏方将“捞女游戏”改名为“情感反诈模拟器”。
争议与热度同时飞升。有人骂它,有人捧它,有玩家调侃这不过是游戏,“让我们男玩家爽一下又怎么啦?”
可这个游戏,真的可以简单看作是男玩家的精神避风港吗?
刷完游戏后,我的答案是:不。
征服:难以抗拒的男性玩家爽点
准确地说,《情感反诈模拟器》需要玩家操作的地方不多,甚至可以把它当成影视剧看,因为玩家只用在剧情关键时刻替男主做选择。从根本上来说,这就是一部男性视角的“爽剧”。
展开剩余92%故事很简单:玩家操作着帅气多金的男主“吴宇伦”,依次俘获一个个“捞女”的心,在情到最浓处抽身离开,对被抛弃的女孩居高临下地留下训诫与惩罚。
游戏中的画面
而且,游戏一开始,就采用了那个最经典的、最能让大部分男性肾上腺素飙升的叙事——莫欺少年穷。
帅气多金的霸总你可能暂时还不是,但“穷小子”的经历是许多玩家都有的吧?好巧不巧,主角吴宇伦,最开始也是个普通穷小子,只能租住在每月500元、没有空调的出租屋里。也正是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,遇到了“捞女”陈欣欣,骗光了男主爷爷的遗产。
画面一转,数年过去,穷困潦倒的吴宇伦翻身成为了“成功人士”,曾经玩弄他于股掌之间的“捞女”,成为他“围猎”的对象。
这一套从落魄到逆袭、从受害者到掌控者的结构,几乎复制粘贴了无数男频网文和都市爽剧的经典叙事逻辑:今天你看不起我,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;你曾伤我至深,我便要你低头认错。
更隐秘的“代入感”,潜藏在一句看似无害的台词里。在游戏开篇,穷小子吴宇伦在面对房东的劝告“带女朋友回来,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”时,他的回答之一是:“如果有爱,她不会介意吧。”
这句“动人的台词”,是游戏借吴宇伦之口,表达了许多男性潜意识里对理想伴侣的择偶愿望:虽然我一无所有,但爱我的她应该愿意陪我吃苦。
游戏里,所有女人都爱上了男主
这样的期待,和“莫欺少年穷”叙事结合在一起,便是许多男性不会陌生的誓言:“贤妻扶我青云志,我还贤妻万两金。”
听起来浪漫,实则是暗含了:作为女性的“你”,得以贤妻为名跟“我”吃苦,并支持“我”。而实际上谁也不能保证“我”真的能成功,那后半句的“万两金”则是纯粹的大饼。
而这些“爽点”还只是前菜。
拿整部游戏第一个出现的“捞女”——女主播唐晓甜来举例。这位从多位“痴情”男性那里骗来大量钱财的“捞女”,偏偏在遇到吴宇伦之后,从“捞女”变成了被捞的“鱼”。面对男主的魅力与金钱攻势,她不仅做小伏低,还无怨无悔地“爆金币”。
这一节故事的最后,被男主魅力所折服的唐晓甜,在得知真相后居然对男主没有丝毫怨怼,甚至愿意继续跟随男主,死心塌地。
对于男性玩家来说,这是何等极致的情绪满足!一个具有“斩男”魅力的美女主播,明明让无数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之下,甚至为她一掷千金、倾家荡产,却偏偏心甘情愿地对“我”低头,为“我”付出。哪怕“我”揭穿她、惩罚她,也依然愿意留在我身边,不离不弃。
这一条情感食物链上,不仅仅是“我”>唐晓甜,更因为唐晓甜>曾经被捞的男人,而变成“我”>唐晓甜>其他男人这样爽到直冲天灵盖的征服关系。
更别说后面还有无数女孩拥护的“女权博主”宋诗琪,也拜倒在男主的魅力下。在男主奢华的家里,两人开始莫名其妙地引用亦舒作品里的句子对谈。他们从亦舒的小说聊到电影与收藏,直到这位骄傲的女人露出崇拜的目光。
更匪夷所思的是,在昏暗的房间里,两人依偎在沙发上看电影,气氛暧昧到一点即燃。
耳鬓厮磨之间,他们开始谈起男主与前女友陈欣欣的感情史……
多么诡异的画面。
很难想象,在这种氛围里,聊天话题居然是男主的前女友
更诡异的是,这位一直坚持在互联网上奋战的“女权博主”,在男主怀里忏悔:“我想了很久,甚至讨厌自己在网上做的那些事情……我现在做的事情,是在摧毁爱情。”
这样的明显有着上下位之分的关系,作为女性,是很难融入其中的,那这种设计只能是为了取悦男性。
对比:情绪化的女人与理性克制的男人
这样的“征服”模式,在男主遇到每一个“捞女”时都会轮番上演。
不管这些女孩曾经有多么骄傲,初见男主时有多么高高在上,剧情走不了几幕,都会自动进入求爱模式:她们渴求男主施舍爱情,面对男主的教育和惩罚,不仅不生气,还要谢过男主“点醒梦中人”。
更离谱的是,在男主拿走她们所有金钱后,她们还会发消息感谢他:谢谢你帮我解脱,我并不怨你。
游戏页面截图
是的,连续剧一般的游戏,人物塑造却扁平得像只为展现男主角孔雀开屏的道具。
有游戏博主试图为游戏辩护,认为它对“捞女”的塑造并非脸谱化,而是洞悉了人性。比如白月光陈欣欣重逢时落泪忏悔、曾真心付出;又比如“捞女组织”中有黑帮背景的何月盈,从小命途多舛、被现实逼上风月之路……听上去,这是一群有血有泪、有故事的女人。
但这些“背景故事”并没有真正赋予她们人性,而更像是为剧情服务的包装纸,无论她们因为什么成为了“捞女”,但不得不承认的是,在这款游戏里,所有女性都是情绪化的、拜金的,甚至是暴力的堕落者。
但反观男性,都是深情的、理性的拯救者,正义的代言人。
拿陈欣欣之死来举例。当她决定洗心革面时,男主不仅不计前嫌,还替她在自己公司里安排了职位,准备跟她开始新的生活。
希望重新开始的陈欣欣,一方面在被男主拯救;另一方面,曾经的“捞女组织”指责她的“背叛”,男主公司里的其他女员工,不断在她背后指指点点。最后陈欣欣在对男主的愧疚中,在浴室里割腕自杀。
这时,游戏里登场的另一位“捞女”、女权博主宋诗琪,在闺蜜死后发起网络声讨,将男主推向舆论风口。但在当面交谈时,男主化身正义使者,严肃批判:“是你这种人在网上煽风点火,断章取义,随意网暴他人。”一旁的另一位女性角色也“看不下去”,指责是宋诗琪的情绪化导致男女无法沟通。
游戏中的宋诗琪
剧情用一次又一次的“情绪女性”对比“理智男主”,制造出一种简单粗暴的性别分工:女性情绪失控、口不择言;男人克制理性、掌控全局。
游戏里的女性,似乎只能靠情感和情绪解决问题。当男主与从事灰色产业的何月盈正面对决时,剧情并没有安排针锋相对的商业博弈,而是走向了幼稚的情感交换:这位掌握地下资源的狠角色,提出的条件居然是让男主做自己的男朋友,随叫随到陪她约会。
当然,若要通关,男主需要毫无动摇,一如既往地高冷抗诱惑。在此期间,美貌的何月盈一次又一次主动挑逗男主,而男主一次又一次在暧昧的拉扯间,坐怀不乱。
是的,游戏里的每一位“捞女”都曾挑逗男主,而吴宇伦始终不为所动,立场坚定地拒绝堕落。
这也是游戏精心安排的另一层“男性爽点”:我不仅是她们的梦中情人,更是她们无法征服的精神高地。
而何月盈则在男主魅力之下,从权势女王沦为情场失意人。她在掌握着男主公司命脉的情况下,依然苦苦哀求男主不要离开自己。在被冷漠拒绝后,居然还发消息道歉,渴求一个与男主见面的机会。
剧情的归宿,自然是吴宇伦高高在上的一次次无情拒绝,以此完成一整套服务某些男性玩家幻想的性别秩序:
她们再骄傲,终究要为“我”低头;她们再聪明,不过也只是一些小手段,逃不过“我”的理性裁决。
影射:披着“游戏”外衣,处处可见现实的影子
面对网络上的批评声,有些玩家觉得这太过小题大做:不就是部游戏吗?用得着这么上纲上线?
但问题是,《情感反诈模拟器》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二次元作品,不是用“纸片人”包装的虚构世界。它是一部真人出演、剧本关联现实、镜头语言极具煽动性的影视游戏。
更确切地说,它是一部披着“互动游戏”外衣的情感连续剧。
这部“连续剧”由香港导演胡耀辉执导,这位导演尤其擅长挖掘现代男女感情和处理大尺度戏份。在《情感反诈模拟器》的镜头里,保留了他惯常使用的拍摄语言——对情欲场景的高频建构和对女性身体的局部凝视。
也就是说,当玩家随着导演的镜头看向游戏里的女性角色时,视角并不是一个平视世界的旁观者,而是用镜头扫视、欣赏和审判一个个女性角色。
这种对女性角色的凝视、审批,并不只停留在剧情之内,而是通过对现实性别争议事件的暗示,输出制作方关于男女关系的价值观点。
游戏开场,就是铺天盖地的社会新闻报道,那些关于“捞女”“情感诈骗”的新闻轮播,拥有完整的新闻要素和熟悉的播音腔,像极了电视上刚刚播报的真实社会案件。
这些假新闻被包装得足够真实,瞬间打破虚拟与现实之间的那堵墙,在几十秒内集中对玩家发出明晃晃的暗示:看,新闻报道上有这么多被“捞女”害惨了的痴心男人!
还有让在以后的剧情中亲口承认自己错了的宋诗琪介绍电影《好芭比》,暗含对电影《芭比》的嘲讽。
就连游戏的角色名字也暗藏着现实的影子。
主角吴宇伦的“白月光”陈欣欣,其姓名就被指出与现实中“翟欣欣案”高度相似。还有去年被官方澄清的“胖猫事件”,其中并没有“捞女设局”,也没有“痴心男”的真心错付。但在《情感反诈模拟器》中,游戏所有章节名的第一个字连起来,便是“愿以后再无彷(胖)猫”。
不仅如此。
游戏里,宋诗琪在网络上控诉男主“渣男”时,男主团队有一段居高临下、意味深长的对话:
吴宇伦:一般被她网暴的男人,会被他搞多久?
员工:老板你放心吧,不会搞多久的,现在网上喷男性的喷子多了,你算老几啊,她们很快会集中火力喷下一个的,你忍忍就过去了。
吴宇伦:一般被她网暴的男人,会被他搞多久?
员工:老板你放心吧,不会搞多久的,现在网上喷男性的喷子多了,你算老几啊,她们很快会集中火力喷下一个的,你忍忍就过去了。
一句“你算老几”,将网络上发表观点的女性简单归结为情绪化的“喷子”,将女性的声音简化为没有持续性的网络噪音。而男性,则始终在情绪的中心,冷静、理智、受害且有分寸。
就像是整部游戏的核心“反捞女”逻辑:女人可以情绪化、可以崩溃、可以忏悔,但最终都要被男性拯救、被男性训诫,乃至被男性使用和定义。
更具讽刺意味的是,到了倒数第二集,剧情开始了所谓的价值观大总结。
男主与“捞女组织”创始人梦娜展开一场对谈。起初梦娜攻击力满满,到最后却点头称赞男主“我们越来越同频了”。这不是因为男主展现了共情、理解、反思,而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关于网络账号的运营方案:“可以创建更多的美女账号,为男性发声。这样不只是可以维持女性流量,也可以获得男性流量。”
多么可笑。在游戏里,男主多次表达“搞男女对立的人,是不配被爱的”,但最后却企图将“女性发声”变成流量工具。
这样的“同频”,暴露出了导演的司马昭之心。
正因为如此,它不能被归类为男玩家自娱自乐的“无害”游戏。
这是毫不掩饰的男性欲望投影,更是一场极具明确指向性的性别仇恨动员:它打着为男性发声为旗号,却“以恨发电”,非常明确地诉诸对女性的仇恨厌恶情绪,再利用这种情绪转化为流量、话题和商业变现的资本。
胡耀辉,这位吃惯了“女性红利”的导演怎么可能不清楚,厌女,依然是互联网上最能变现的情绪燃料之一。
发布于:四川省耐思徳配资,配资网炒股,新型股票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